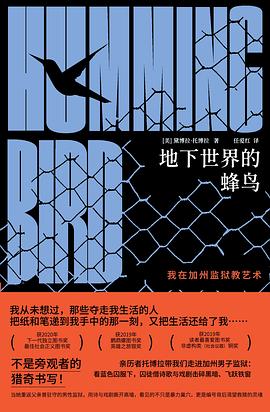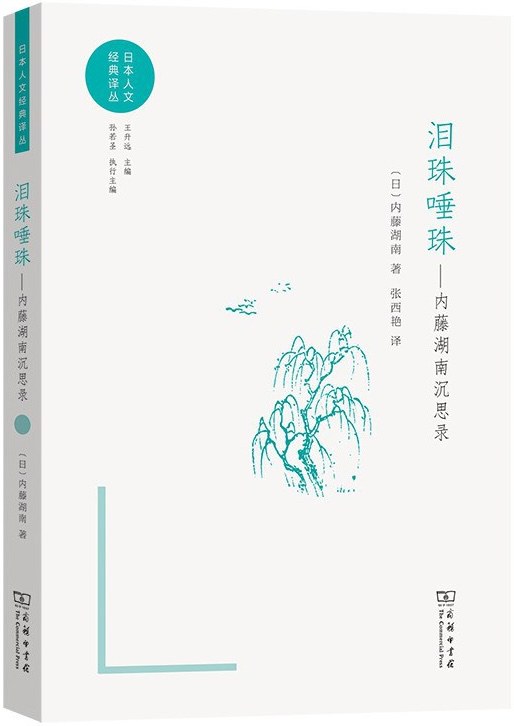地下世界的蜂鸟—-在铁丝网与高墙的阴影下,我们是否有权仅仅作为“人”而存在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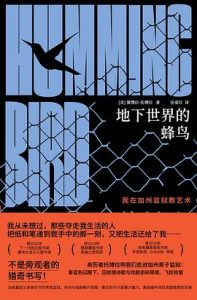
作者: [美] 黛博拉·托博拉
出版社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品方: 北京贝贝特
副标题: 我在加州监狱教艺术
原作名: Hummingbird in Underworld: Teaching in a Men’s Prison
译者: 任爱红
出版年: 2025-11
定价: 58.00
装帧: 精装
ISBN: 9787559889249
|从一声沉闷的关门声说起
如果你曾有机会站在一座重刑监狱的门前,最先震慑你的往往不是荷枪实弹的警卫,而是那种特有的、仿佛能将空气都切割开来的声音——巨大的金属闸门在身后重重合上,发出“哐当”一声。在那一瞬间,你被从“自由世界”物理性地剥离,进入了一个折叠的、不见天日的“地下世界”。
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路易斯-奥比斯波,有一座被称为“男人的殖民地”(California Men’s Colony)的监狱。对于大多数路过的一号公路游客而言,那只是一片冷峻的建筑群;但对于黛博拉·托博拉(Deborah Tobola)而言,那是她工作了九年的地方,是她试图用诗歌与戏剧去敲开的一个坚硬的黑盒。
她的非虚构新作《地下世界的蜂鸟》(Hummingbird in Underworld),并不是一本猎奇的犯罪实录,也不仅仅是一份关于美国司法体制黑洞的控诉状。它更像是一份充满了痛感与温柔的人类学田野笔记,记录了在那个被社会遗弃的“非人”空间里,艺术是如何作为一种最为顽强的生命形式,在水泥缝隙中开出花来的。
|剥去“囚犯”的标签,看见“蜂鸟”的振翅
作为一名曾经的记者、诗人,托博拉在45岁那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:进入父亲曾经工作过的监狱,不是做狱警,而是担任“艺术指导”。这个职位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一种荒诞的张力——在一个旨在剥夺自由、强调规训的暴力机构里,教授关于自由与表达的艺术,这无异于在荒原上播种玫瑰。
书中最打动我的,是作者对于**“命名权”**的争夺。
在监狱的行政逻辑里,里面的人只有一个名字:囚犯(Inmate),或者是一串冰冷的编号。这个词抹除了一切个体差异,将活生生的人简化为需要被管理的肉体。但在托博拉的创意写作课上,她将被判终身监禁的杀人犯、抢劫犯重新命名为“诗人”、“剧作家”、“画师”。
这种称呼的转换并非是一种廉价的政治正确,而是一种本体论上的拯救。书中描写的那些角色——抢劫披萨店的大学生奥皮、背负谋杀罪名的剃刀(Razor)、才华横溢却深受童年创伤的亚历杭德罗——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是绝对的“恶”,但在那个狭小的教室里,当他们朗读起自己写的诗句时,他们展现出了令人心碎的脆弱与高贵。
“在地下世界,我们都是折翼的鸟。但即使是在地狱的最深处,依然有蜂鸟在振翅。”
这个隐喻贯穿全书。蜂鸟,这种世界上最小、心跳最快的鸟类,象征着一种在极度受限的空间里依然能保持高频振动、依然能悬停并吸食花蜜的能力。这正是书中那些“囚犯艺术家”的生存状态:肉身被禁锢在铁笼之中,但灵魂却通过艺术的虫洞,完成了不可能的飞翔。
|当代的环形监狱与“可见性”的政治
将这本书置于更大的社会脉络中,它回应了米歇尔·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提出的核心议题:现代监狱是如何通过“全景敞视”来制造顺从的肉体的。
美国作为世界上监禁率最高的国家之一,其司法体系往往被批评为一种“报复性正义”而非“修复性正义”。在这个庞大的工业复合体中,人被异化为数据。托博拉敏锐地观察到了监狱内部那堵无形的“绿墙”(Green Wall,指狱警之间的沉默守则与权力结盟),这堵墙不仅隔绝了囚犯与自由,也隔绝了囚犯与“人性”。
《地下世界的蜂鸟》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它通过“可见性”挑战了这种权力结构。当囚犯们在托博拉的指导下排演戏剧,甚至邀请外界观众进入监狱观看时,一种奇妙的**“阈限体验”**发生了:坐在台下的自由人,看着台上穿着囚服的演员,那一刻,善与恶、自由与禁锢的边界变得模糊。观众被迫直视那些被他们抛弃的人,并在对方的眼泪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。
这种**“艺术介入”**(Arts in Corrections)的实践,是对当代社会日益严重的原子化与排他性的一种深刻反思。它提醒我们,正义不应止步于惩罚,更应包含了对破碎人性的缝补。
|为何我们不敢直视深渊?
阅读这本书的过程,并不轻松。作者没有回避那些罪犯曾经犯下的残暴罪行,也没有陷入廉价的圣母式感动。她真实地记录了监狱中的暴力、帮派斗争以及那些令人绝望的时刻——当你精心辅导的学生因为一次违禁品搜查而被关进禁闭室,所有的努力似乎瞬间归零。
但正是这种**“无力感”**,构成了本书最深沉的力量。它迫使读者去思考一个我们极力回避的问题:那些被关进笼子里的人,是否就彻底失去了作为“人”的资格?如果我们剥夺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,剥夺了他们接触美的权利,那么我们与我们所谴责的野蛮之间,究竟还剩下多少距离?
在这个“取消文化”盛行、人们急于站队审判他人的网络时代,托博拉的文字提供了一种稀缺的**“复杂性”**。她告诉我们,人性不是非黑即白的,在最幽暗的地下世界,依然有人渴望着光。
|结语:在墙的裂缝中,种下一株风信子
合上《地下世界的蜂鸟》,那声沉闷的关门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。但这一次,你或许会听到另一种声音——那是蜂鸟翅膀极速振动的嗡嗡声,是生命在窒息中依然坚持呼吸的证明。
这本书不仅是为了那些狱中的灵魂而写,更是为了墙外的我们而写。它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我们社会对待“异类”的态度。或许,真正的自由并非仅仅是身体的无拘无束,而是拥有一颗能够跨越偏见、在废墟中辨认出人性光辉的心。
当我们在阳光下自由行走时,请不要忘记,在地下世界的深处,仍有蜂鸟在等待一次起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