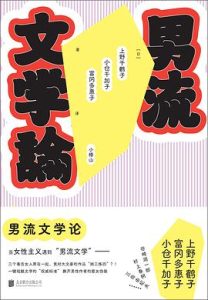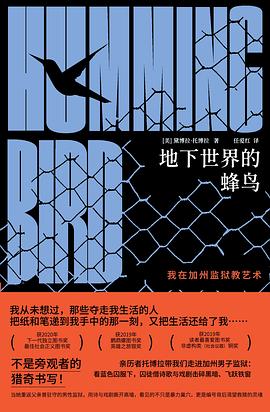从厌女症到防卫:日本近代文豪的伦理叙述危机与当代主体困境
在当代日本思想的版本图上,文学常被视为男性主体确立自我、构建秩序的祭坛。然而,1992年由上野千鹤子、小仓千加子与富冈多惠子合着的《男流文学论》,类似于一把冰冷的手术刀,切开了这个由性别特权构筑的血肉纹理的祭坛。
门槛下的性别共谋:当“私小说”遭遇女性凝视
长期以来,日本文学界着着一种默契:以男性为核心的写作被冠以“普遍性”的桂冠,而女性写作则常被边缘化为“女流文学”。上野千鹤子等三位作者在书中,以“男流文学”这一挑衅性的存在完成了权力的移转。这种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:这将男性写作从“常态”转变为“多重性别的局部叙事”。
从社会学视角看,这种分析不仅是对文学的解码,更是对日本近代化进程中“男权主体性”的回溯性的审视。书评的切入点,正是在于这种“主体性”的虚弱与伪饰。
文本细读:在“求道”与“女厌”之间
书中围绕六位巨匠——吉行淳之介、岛尾敏雄、谷崎润一郎、小岛信夫、村上春树、三岛由夫——的文本进行了胁迫的“细读”(闭读)。
在讨论吉行淳之介时,小仓千加子敏锐地指出其作品中女性快感的自我意向性。吉行笔下的性爱并非两个主体的交锋,而是一个男性在想象的镜面中进行的确认。上野千鹤子则更进一步,揭示了这种所谓“性的求道者”姿态,本质上是小拟人的虚无,其笔下式的女性呻吟不过是为了内心深处的“厌女症”(憎女症)。
而对于岛尾敏雄的《死之棘》,评论锋芒直指那种“以爱为名的软禁”。岛尾将妻子的狂气转化为文学养分,这种“诚实”在三位作者眼中是一种极大的暴力——他将对方束缚在狂徒的位置上,从而完成了自己作为受难者的神化。这种叙述伦理的束缚,在她们的对话中被拆解为“近代性爱的双重束缚”。
甚至连当时风头正劲的村上春树也未能幸免。在《挪威的森林》的章节关系中,渡边君被定义为一个“黑洞”,其标志性的“呀哩呀哩”(やれやれ)并非超脱,而是一种拒绝进入坚强的自我防卫。这反映了80年代后日本社会中那种“互不关联”的疏离感。
延伸:作为批评武器的逻辑逻辑
《男流文学论》的精彩不仅提出了观点,更提出了三位女性知识分子的“纠缠”式对话。上野的社会学解构、小仓的心理学视角与富冈作为创作者的内部批判,构成了一种**批评的雌雄同体(雌雄同体)**状态。
她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:许多其实被推崇为经典的日本文学,是建立在对女性的“非人化”处理之上的——或是作为泄欲的人形(吉行),或是作为疯狂的巫女(岛尾),或是作为悲伤的符号(村上)。
现实意义:新自由主义时代的“自我异化”
当代,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回到了过去。在当今社交媒体驱动的“自我呈现”时代,男性主体构建了对他者的消费与抑制的依然隔绝依赖。书中对三岛纪夫“逻辑性自杀”与“厌女本质”的探讨,精准地捕捉到了那种因无法忍受“平庸而有用的自我”而产生的主体焦虑。
《男流文学论》提醒读者:文学隐藏从不是空白中产生的纯粹审美。每一个优美的隐喻背后,可能都着着一套权力结构的压迫逻辑。当我们重新阅读那些经典时,是否能像这三位作者一样,在赞叹文笔的华丽之余,亦能剖析其贫乏的性别原罪?
这种批评并非是为了埋葬文学,而是为了重构一种重新开放性的主体叙述。在“男流”之外,我们期待的是一种不再以牺牲他者为代价的、真正的生命表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