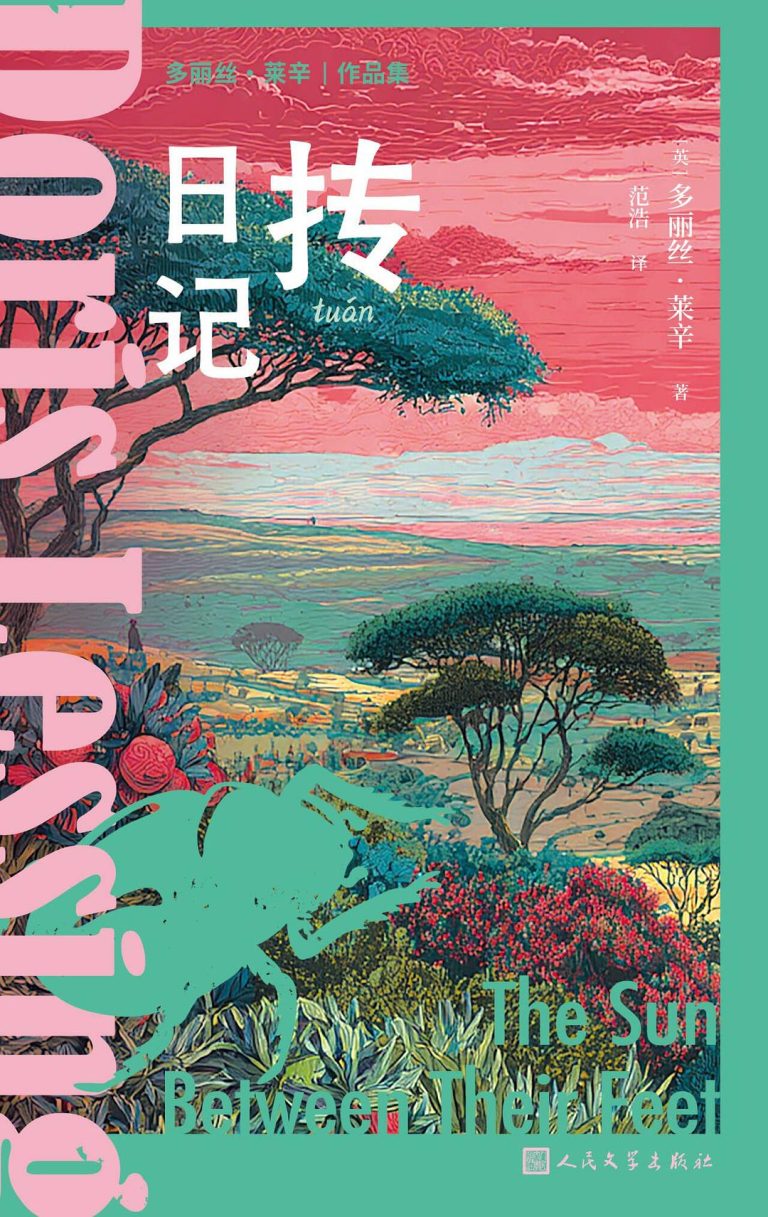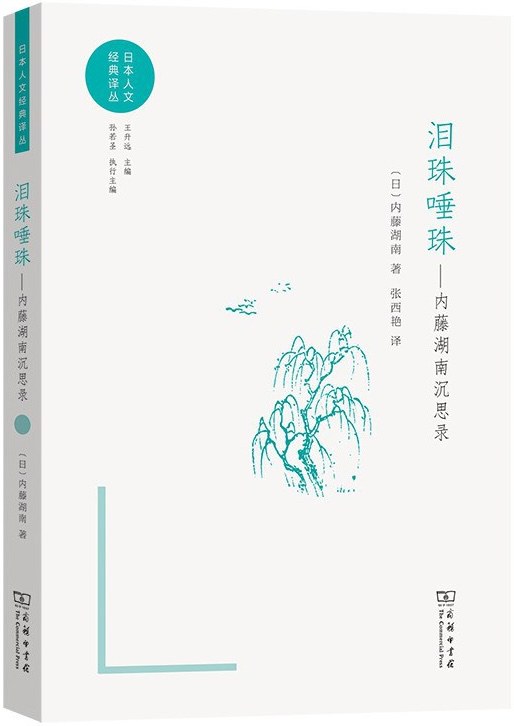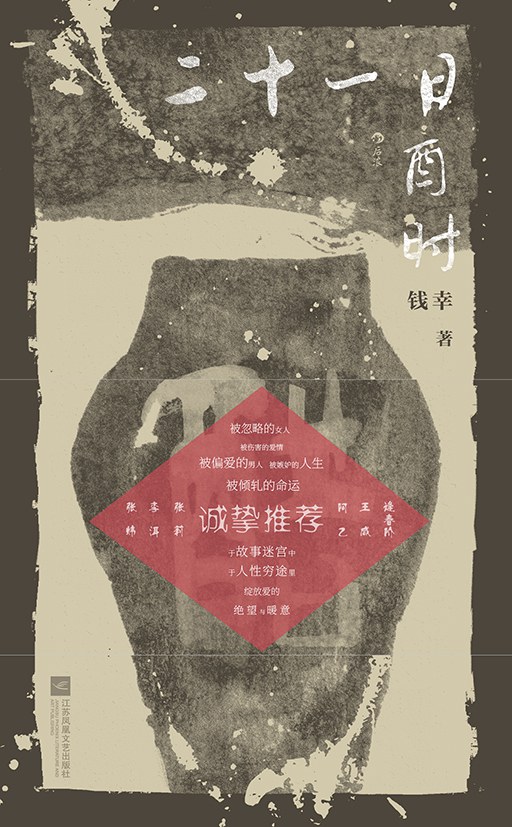穿越十万年的虚无凝视:当爱只是一种古老的生存算法—-评《我的恋人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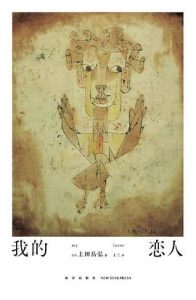
|从约会软件上的那一次“左滑”说起
在Tinder或探探这类约会软件上,我们习惯了以一种极其高效且冷酷的方式审视他人:一张磨皮过度的照片、一句精心修饰的签名。只需拇指轻轻一划,一个具体的人就被归档为“感兴趣”或“垃圾”。这种现代择偶机制虽然便捷,却常让人感到一种深层的生理性疲惫——仿佛我们不再是寻找灵魂伴侣的人类,而是正在执行某种匹配程序的生物机器。
如果我们将这种疲惫的时间轴拉长,拉长到十万年,会看到什么?
日本作家上田岳弘(Ueda Takahiro)的小说《我的恋人》,正是提供了一双**“穿越深时(Deep Time)”的眼睛**。在这位三岛由纪夫奖得主的笔下,那种想要寻找“恋人”的冲动,不再是荷尔蒙的躁动,而是一场跨越了旧石器时代、二战时期直至现代平成年间的漫长迁徙。他用一种近乎非人的冷静,审视着那个名为“爱”的古老算法,如何在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,驱动着我们走出非洲,填满地球的每一个角落,最终却在现代都市的公寓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。
|作为“容器”的主角与后人类的凝视
上田岳弘的小说总是带有一种令人战栗的**“高空视角”**(Overhead View)。
在《我的恋人》中,主人公井上由佑拥有三世的记忆:第一世是十万年前克罗马农人洞穴里的先知,第二世是二战时期被关进收容所的犹太人,第三世则是生活在东京、正如你我一般平庸的35岁上班族。
这种设定并非为了上演一出廉价的“穿越剧”,而是为了构建一种独特的叙事伦理。作者通过主角那双**“老灵魂”的眼睛**,将现代生活彻底陌生化了。在他眼中,现代人那种为了加班、为了房贷、为了社交网络上的点赞而焦虑的日常,显得如此滑稽而又悲哀。
书中有一个核心隐喻:人类的“伟大旅程”(Great Journey)。十万年前,我们为了生存而迁徙;十万年后,我们在物质极度丰裕的今天,依然在精神上流离失所。主角对“恋人”的追逐,实际上是对**“原初生命力”**的一种乡愁。那个在第一世中浑身长毛、充满野性的恋人,到了这一世变成了一个致力于反捕鲸运动的激进分子。这种变形本身,就是对文明进程的一种绝妙讽刺——我们褪去了兽性的毛发,学会了穿西装、用刀叉,但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想要“连接”的原始兽性,却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迷路了。
|在绝对的理性中,爱是唯一的BUG
上田岳弘的文笔具有一种**“手术刀般的冰冷”**。他不像传统日本私小说那样沉溺于情绪的泥沼,而是用一种近似说明书的语言来解构情感。
在他的笔下,人被还原为生物学意义上的“肉块”与“数据”。这种写法让人想起科幻作家菲利普·K·迪克或电影《发条橙》,带有一种后人类主义(Post-humanism)的疏离感。
然而,正是这种极致的理性,反衬出了“爱”的荒谬与珍贵。在书中,主角意识到,尽管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可以轻易毁灭地球的地步,尽管我们发明了无数种逃避孤独的娱乐方式,但唯有“寻找恋人”这一本能,是我们无法被理性驯化的系统BUG。
那个“恋人”或许并不存在于具体的某个人身上,她是一个符号,象征着那个永远无法抵达的“他者”。我们在十万年的进化中,杀戮、繁衍、建设、破坏,其实都只是为了在茫茫宇宙中,向那个未知的“他者”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呼喊。
|为何在这个“倦怠社会”重读上田岳弘?
在2026年的当下,我们正处于韩炳哲所说的“倦怠社会”的晚期。我们活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长(主角感叹自己终于活过了前两世未曾达到的35岁),但也比任何时期都更为空虚。
阅读《我的恋人》,是一次对这种现代虚无症的休克疗法。它强迫我们跳出那个狭隘的“自我”,站在卫星轨道的高度俯瞰自己的人生。当意识到你的每一次心动、每一次失恋,都是那场延续了十万年的宏大迁徙的一部分时,你或许会感到一种释然——原来我们的孤独不是个人的失败,而是人类作为一种物种的宿命。
|结语:在进化的尽头,等待一次回眸
合上书页,你会发现窗外的霓虹灯似乎变得不再那么刺眼,街上行色匆匆的路人也变得不再那么面目可憎。
因为你知道,在那层光滑、精致的现代皮肤之下,我们依然是那个在荒原上瑟瑟发抖、渴望在篝火旁找到另一个同类的克罗马农人。我们依然在等待那个穿越了十万年的恋人,在时间的尽头,回过头来,看我们一眼。